 文章類別: 文章類別: |
|
|
|
| |
廣告:120元/月/條 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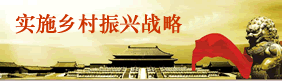 |
|
 |
當(dāng)前類別 >
管理培訓(xùn)文庫> 宗教哲學(xué)與管理 |
|
| 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
|
| 宗教哲學(xué)與管理: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,宗教哲學(xué)與管理: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,宗教哲學(xué)與管理: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,宗教哲學(xué)與管理: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,
|
|
| |
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
論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
張松輝
提要:
本文認為道家的內(nèi)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(zhí)著在實質(zhì)內(nèi)容上是一致的,只不過禪宗論述得更為詳盡而己。這些理論都是為解決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服務(wù)的,在理論闡述上十分圓通,但在現(xiàn)實實踐中,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做到這一點。
張松輝,1953年生,哲學(xué)博士,湖南師范大學(xué)中文系主任,教授。
主題詞:內(nèi)圣外王不執(zhí)著除境除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"齊萬物"和"不分別"是觀察事物的方法,道、佛兩家通過這些方法,目的是要達到"內(nèi)圣外王"和"不執(zhí)著"的人生境界。人生活在世界上,必須和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事打交道,對此,無論是世內(nèi)人還是世外人都是承認的。和人、事打交道時,畢竟會有順心的,也有不順心的,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影響一個人的情緒。情緒有了波動,道家就擔(dān)心會影響自己的生命質(zhì)量和身體健康,而佛教也擔(dān)心會影響自己的得道成佛。于是有的道家人士主張進入深山老林,有的僧人主張空物空心,而事實上深山老林依然是社會的一部分,空物空心也依然要和心物交往。所謂的世外人,是不可能真正地生活在世外的,既要做世俗人所要做的事情,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世外人的清靜,這是一對很難解決的矛盾。而道家的"內(nèi)圣外王"和佛教的"不執(zhí)著",就是為解決這一矛盾服務(wù)的。二者字面意思不同,本質(zhì)內(nèi)涵一致。
>>>> 清華大學(xué)--中國企業(yè)家精修課程
一、道家的最高境界:內(nèi)圣外王
"內(nèi)圣外王"的主張是《莊子·天下》首先提出來的,但在莊子那里,這個理論闡述得還不夠成熟,莊子在運用這一理論處理具體問題時也不夠圓通。一直到晉朝的郭象時,這一理論才得到了圓滿的解釋。
關(guān)于"內(nèi)圣外王"的含義,郭象在《莊子注》中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,他說:
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,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,世其識之哉?徒見其戴黃屋,佩玉璽,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;見其歷山川、同民事,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;豈知至者之不虧哉!
這種內(nèi)圣外王之道,可以說是人的最高生活境界。所謂的"內(nèi)圣",是指養(yǎng)神藝術(shù),不管這個人在現(xiàn)實中正在做什么,只要能夠做到"內(nèi)圣",他就能夠在精神上超越現(xiàn)實中的一切,在精神上達到逍遙自由的出世目的;"外王"是政治領(lǐng)導(dǎo)藝術(shù),雖然這個人主觀上無意于做事,但在客觀現(xiàn)實中,他卻把一切該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條。這就是說,思想境界最高的人,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樂,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。
《莊子·逍遙游》中講了一個故事:堯在當(dāng)天子期間,看到著名隱士許由的道德比自己更高尚,于是他就主動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帝位讓給許由,而許由認為"鷦鷯巢于深林,不過一枝;偃鼠飲河,不過滿腹。……予無所用天下為!"表示自己決不會越俎代庖去當(dāng)?shù)弁酢?jù)《史記"正義"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說,其后還發(fā)生一個有趣的故事:
許由字武仲。堯聞,致天下而讓焉,乃退而遁于中岳穎水之陽、箕山之下隱。堯又召為九洲長,由不欲聞之,洗耳于穎水濱。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,見由洗耳,問其故,對曰:"堯欲召我為九洲長,惡聞其聲,是故洗耳。"巢父曰:"子若處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誰能見子?子故浮游欲聞,求其名譽,污吾犢口。"牽犢上游飲之。許由歿,葬此山,亦名許由山,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。
毫無疑問,包括莊子在內(nèi)的許多人都認為許由的品質(zhì)比堯更為高潔,因而也更應(yīng)該受到贊揚。而郭象認為許由的思想境界遠遠比不上堯的高,因為許由偏執(zhí)于一端,不能做到順其自然。郭象在他的《莊子注》中說:
夫自任者對物,而順物者與物無對,故堯無對于天下,而許由與稷、契為匹矣。
所謂"對物",就是不能順應(yīng)客觀環(huán)境而同客觀環(huán)境對立起來。在郭象看來,堯是"內(nèi)圣外王"的典范,他能夠順物而行,該做天子的時侯就做天子,該禪讓的時侯就禪讓,沒有把自己的意志同社會需要和客觀環(huán)境對立起來;而許由與稷、契在具體行為上雖然不同,許由力主出世,稷、契積極入世,但他們心中同樣有"我",有一個固執(zhí)的成見,沒能做到順物而行,因而也就沒有做到"內(nèi)圣外王"。
后來,不少文人對這一看法持欣賞態(tài)度,并以此作為自己的處世原則。王維寫了一篇《與魏居士書》,在這封信中,他勸告魏居士要走出山林,進入朝遷。王維要求對方這樣做的根據(jù)就是"內(nèi)圣外王",認為只要"身心相離,理事具如,則何往而不適?"他同樣舉許由為例,說:"古之高者曰許由,……聞堯讓,臨水而洗耳,耳非住聲之地,聲無染耳之跡;惡外者垢內(nèi),病物者自我,此尚不能至于曠士,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,亦云頓纓狂顧,逾思長林而憶豐草。頓纓狂顧,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?長林豐草,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?"王維認為,像許由、嵇康這一類堅決拒絕出仕、一心向往隱士生活的人,邊一個曠達之士都算不上,更談不上在道德修養(yǎng)方面登堂入室了。人應(yīng)該視出仕與入世為一,看官署與山林無二,無論處于何等境地,都能適心如意,這才算是做到了內(nèi)圣外王。王維的后半生即過著亦隱亦仕的生活,可以看作是對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。
白居易是另一位有如此胸懷的大詩人,他自己曾說過:"余早棲心釋梵,浪跡老莊。"(《病中詩十五首序》)因此他深受莊子"內(nèi)圣外王"之道和佛教"不執(zhí)著"思想的影響,主張過一種"無可無不可"的生活。他在詩中說:
道行無喜退無憂,舒卷如云得自由。(《和楊尚書》)
若論塵事何由了,但問云心自在無?進退是非俱是夢,丘中闕下亦何殊?
(《楊六尚書頻寄新詩,詩中多有思閑相就之志。因書鄙意,報而諭之》)
他多次以云自比,認為自己能夠像舒卷自由的白云那樣因物賦形,隨遇而安,并不固執(zhí)地一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。
王維和白居易都是從大處談?wù)?內(nèi)圣外王"之道,而蘇東坡還把"內(nèi)圣外王"之道貫徹到了日常生活小事之中,他曾寫了一篇《劉凝之與沈麟士》:
《南史》: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,即與之。此人后得所失屐,送還,不肯復(fù)取,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屐,麟士笑曰:是卿屐耶?即與之,鄰人后得所失屐,送還之。麟士曰:"非卿屐耶?"笑而受之。此雖小節(jié),然人處世,當(dāng)如麟士,不當(dāng)如凝之也。
索則與,與則取,這才算是通達而不固執(zhí);索則與,與而不取,只能算是半個通達,因而受到蘇東坡的批評。
簡單地說,內(nèi)圣外王就是要求人們在和外界交往時,形體上忙忙碌碌、嚴肅認真,而精神上卻保持著愉悅的狀態(tài)。而要做到這一點,首先就要做到順應(yīng)外物,心中不要有"我"。
二、禪宗的最高境界:不執(zhí)著
"不執(zhí)著"是禪宗的一個命題,其內(nèi)涵與"內(nèi)圣外王"差不多,只是在表達方式上顯得更圓通、更明白一些。
禪宗認為,高僧大德的生活與一般人的生活,從表面上來看,沒有太大的不同,都是在"著衣吃飯,屙屎送尿"(《古尊宿語錄》卷四),不同的是他們在著衣吃飯時的心態(tài)。一般人"吃飯時不肯吃飯,百般須索;睡時不肯睡,千般計較"(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六)。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,世俗人由于欲求過高,名利心過重,整日在算計別人,以有利于自身,于是他們吃飯不感到香甜,睡覺時總是失眠,他們的精神負擔(dān)太重。或者是因為他們對事物分別得太清楚,好的就吃下去,不好的就難以下咽。而高僧卻是另一番景象:
終日吃飯,未曾咬著一粒米;終日行,未曾踏著一片地。與么時,無人無我等相。終日不離一切事,終日須事,不被諸境惑,方各自在人。(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)
終日說事,未曾掛著唇齒,未曾道著一字;終日著衣吃飯,未曾觸著一粒米,掛著一縷絲。(《古尊宿語錄》卷十五)
高僧們也要吃飯,也要穿衣。所謂的不咬著一粒米,不曾掛著一縷絲,不是指他們的肉體,而是指他們精神上的一種感受。也就是說,當(dāng)他們的肉體在吃飯穿衣的時候,而他們在精神上并不執(zhí)著于吃飯穿衣。
禪宗還效法莊子和玄學(xué),提出了"即世間而求出世間"的主張,認為只要內(nèi)心清靜無為,即使不出家,即使日理萬機,照樣可以得道成佛。唐代著名禪師弘辨對唐宣宗說:"陛下日理萬機,即是陛下佛心。"(《五燈會元》卷四)另如唐代吳居厚趕考路過鐘陵時曾向老禪師請教佛法,禪師教他"且去做官",五十余年以后,吳居厚持節(jié)歸鐘陵,再謁圓通竁禪師。他坦率地對禪師說:自己一直在思考訥老禪師的話,但一直沒有參透,也一直沒有瀟灑起來。圓通竁禪師就遞給他一把扇子,吳居厚就搖起扇子,禪師當(dāng)即發(fā)問:"有甚不脫灑處?"據(jù)說吳居厚聽后即有所醒悟(見《五燈會元》卷十八)。禪宗在傳法時,有一個"不說破"的習(xí)慣,因此,他們的話聽起來有一種故弄玄虛的味道。弘辨禪師、訥老禪師、圓通竁禪師的話都沒有"說破",但實際意思是一致的,那就是要求人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內(nèi)心的清靜。世人即使日理萬機,官事鞅掌,只要心中不執(zhí)著,那就自由自在、逍遙灑脫的真佛。
六祖惠能禪師很主張在家修行,他認為無論在家在寺,只要一念不起,都可成佛。《壇經(jīng)》記載了他寫的一首偈語:
正見名出世,邪見是世間。邪正盡打卻,菩提性宛然。
邪見固然不好,但如果執(zhí)著于正見,同樣不好。只有在心中既不存在邪見,也不存在正見,那才算是擦凈了自己的天然本性。所以惠能反反復(fù)復(fù)地要求人們既不能心存惡念,也不能心存善念。不存惡念容易理解,但為什么也要不存善念呢?佛祖不是要求修行要以慈悲為懷、普救眾生嗎?但禪宗自有禪宗的道理:
師(惟寬禪師)曰:"心本無損傷,云何要修理?無論垢與凈,一切勿念起。"(白居易)曰:"垢即不可念,凈無念可乎?"師曰:"如人眼睛上,一物不可住。金屑雖珍寶,在眼亦為病(《五燈會元》卷三)
禪宗認為,人心好比眼睛,眼睛固然不能揉進砂子,但也不能揉進金屑。金屑比砂子要珍貴得多,但同樣傷害眼睛。白居易在《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銘并序》中也記載他向惟寬禪師提出了四個問題,其中第三個就是這個問題。心里老記掛著我要做到善、善、善,我要排除惡、惡、惡,這同樣是執(zhí)著,同樣瀟灑不起來。
我們打一個比方,可能會把"內(nèi)圣外王"和"不執(zhí)著"的道理講得更明白一些。能夠做到內(nèi)圣外王和不執(zhí)著的人內(nèi)心就像廣大無垠的虛空,無論什么東西放進這個虛空,虛空都會無限寬容地接受它們,不予拒絕。當(dāng)這些東西離開虛空時,虛空也不留戀。同樣的,當(dāng)這些東西存在于虛空的時侯,也不會對虛空造成任何的傷害。因為虛空是無"心"的,它對這些東西的大小好壞都是不加區(qū)別的。關(guān)于這一點,莊子也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:
至人之用心若境,不將不迎,應(yīng)而不藏,故能勝物而不傷。(《莊子·應(yīng)帝王》)
思想境界最高的人,其心就像一面鏡子,它不去主動地迎接萬物,也不主動地去送走萬物,萬物來了,它就照一照,萬物走了,它自己也不會因此而留下任何痕跡。正是由于至人能夠保持這種"虛"的精神狀態(tài),所以它們在精神上從來就不會受到任何的傷害。
同莊子相比,禪宗還向前進了一步。禪學(xué)大師們不僅要求人們"不執(zhí)著",而且還要求人們不執(zhí)著于"不執(zhí)著'。也就是說,一個人如果老念念不忘地去告誡自己:我不要執(zhí)著于名利!我不要執(zhí)著于名利!在大師們看來,這樣的人的功夫還遠遠不到家。一個思想境界真正高妙的人,他不僅忘記了"名利",而且還忘記了"我不要執(zhí)著于名利"這條道德準(zhǔn)則本身。一個需要時刻自己遠離名利的人,他實際上還沒擺脫名利的束縛。
最后附帶提到一點,就是佛教還把這種不執(zhí)著的"無心"狀態(tài)運用到學(xué)佛方面:
若起精進心,是妄非精進,若能心不妄,精進無有涯。(《五燈會元》卷二引《法句經(jīng)》)
這四句偈語的意思是:如果一個人時刻不忘記努力學(xué)佛,這是錯誤的;只有當(dāng)他努力學(xué)佛的時候而又忘記了自己是在努力學(xué)佛,他才能不斷進步,前途無量,這對于我們的學(xué)習(xí)具有很大的啟發(fā)意義,和我們常說的"只問耕耘,不求收獲而收獲自有"有相通之處。
三、說得行不得:內(nèi)圣外王與不執(zhí)著思想的艱難實踐
達到"內(nèi)圣外王"和"不執(zhí)著"的關(guān)鍵是什么呢?唐代的大珠慧海禪師明代的屠隆都進行過很好的概括。他們說:
圣人求心不求佛,愚人求佛求心;智人調(diào)心不調(diào)身,愚人調(diào)身不調(diào)心。(慧海禪師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)
至人除心不除境,境在而心常寂然;凡人除境不除心,境去而心猶牽絆。(屠隆《娑羅館清言》卷下)
思想境界真正高尚的人,注意力主要放在清掃自己的心境,心境打掃干凈了,即使身處名利場上,也不會受到名利的污染。還有一些假隱士逃進深山老林,竭力逃避名利場,但如果不把心境打掃干凈,他們依然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。說到底,要想做到內(nèi)圣外王,要想做到不執(zhí)不著,關(guān)鍵都在于一顆"心"。
《古今談概·迂腐部》"心中有妓"一條很能說明這一問題:
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,有妓侑觴。伊川(弟程賾,世稱伊川先生)拂衣起,明道(兄程顥,世稱明道先生)盡歡而罷。次日,伊川過明道齋中,慍猶未解。明道曰:"昨日座中有妓,吾心中卻無妓;今日齋中無妓,汝心中卻有妓。"伊川自謂不及。
二程是著名的理學(xué)家,但也深受佛道的影響,主張"心中無妓",這實際上就是一次"至人除心不除境"的實踐。程顥做到了"除心不除境",所以他能夠心平氣和地對待不適合于自己的客觀環(huán)境;而程頤是"除境不除心",所以無論妓女在場還是不在場,他都憤憤不平。
內(nèi)圣外王之道和不執(zhí)著的思想的確在理論上非常圓滿地解決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。我們之所以強調(diào)"在理論上"這一點,意思是說,內(nèi)圣外王和不執(zhí)著這種境界可以在理論上談一談,而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,不要說是作為一國之王的"王",即便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,面對著社會人性、衣食需要……,要想保持古井般平靜心,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莊子是第一個提出"內(nèi)圣外王"之道的人,他同樣做不到這一點。當(dāng)楚王邀請他前去做官時,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,堅決予以拒絕。他執(zhí)著于當(dāng)隱士。郭象是第一個對"內(nèi)圣外王"之道進行圓滿解釋的人,但他在有權(quán)之后,"熏灼內(nèi)外,由是素論去之"(《晉書飯ó傳》),當(dāng)時就受到人們的鄙視。而且郭象在學(xué)問上,也堪稱抄襲大家,據(jù)《晉書》記載,向秀曾注釋《莊子》,只剩《秋水》、《至樂》兩篇沒有完成。向秀死時,其子還小,不知繼承父業(yè),于是郭象便盜取向秀的《莊子注》,稍加整理補充,據(jù)為己有。由此可見,郭象對名利是相當(dāng)看重的。
僧人們在實踐自己的不執(zhí)著理論時,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。我們看《五燈會元》卷二的一段記載:
溫州凈居尼玄機……念曰:"法性湛然,本無去住,厭喧趨寂,豈為達邪?"乃往參雪峰。峰問:甚處來?曰:"大日山來。"峰曰:"日出也未?"師曰:"日出則熔卻雪峰。"峰曰:"汝名甚么?"師曰:"玄機。"峰曰:"日織多少?"師曰:"寸絲不掛。"遂禮拜退,才退三五步,峰召曰:"袈裟角拖地也。"師回顧。峰曰:"大好寸絲不掛。"
玄機被禪宗視為一位女高僧,不然,《五燈會元》也不會專為她立傳。玄機說自己"寸絲不掛",用意與"終日著衣,未曾掛著一縷絲"一樣,即認為自己已經(jīng)達到了毫不執(zhí)著的境界。為了印證這一點,雪峰大師趁她不注意的時候,突然對她說:"你的袈裟拖在地上了。"如果玄機在心中真的做到了無物痕,那么袈裟拖不拖在地上,她將毫不在意。然而她沒有做到這一點,當(dāng)聽到別人的提醒時,她回頭看了,看自己的袈裟是不是真的拖在了地上。這回頭,就充分說明她還沒有真正在精神上做到"寸絲不掛"。
據(jù)《祖堂集》、《古尊宿語錄》等書記載,五代時的存獎禪師深受唐莊宗的賞識,莊宗賜給他一匹好馬,存獎禪師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,一條腿成了殘廢。在他臨死之前,拄著拐杖繞院一周,然后對徒弟們說:"疬腳法師,說得行不得。"這是對自己,也是所有禪師的一次十分坦率而嚴厲的解剖。在這個世界上,說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。據(jù)說印度的奧修二十一歲的時候就"開悟",被稱為"智者"。他在《虛舟》中有這么一段話:
現(xiàn)在科學(xué)家已計算出,一個成功人士到四十歲就應(yīng)當(dāng)有潰瘍,到五十歲應(yīng)當(dāng)有第一次心肌梗塞。到六十歲他就走了--而他從來沒有活著過。沒有時間來活。他有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,沒有時間來湃。
奧修是帶著譏諷的口氣來講這段話的。他認為有些人一生陷于名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,從來沒有享受過生活,整天在算計,在操勞,所以他們只能活到六十歲。我很贊成奧修的這一見解,同樣認為所活年齡的大小是衡量一個人心胸寬廣或狹窄的標(biāo)準(zhǔn)之一。奧修明白這一點,但他做到了這一點嗎?據(jù)有關(guān)資料介紹,奧修在擔(dān)任九年大學(xué)哲學(xué)教授之后,就周游各地演講,根據(jù)他的演講已出版了650多冊(種)書,并被譯成32種文字行銷世界各地。奧修生于1931年12月,死于1990年1月,只活了59歲,連他所諷刺的六十歲都沒達到。這樣一個事實對于所謂的"智者"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嘲弄。
從古到今,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絕對的"內(nèi)圣外王"和"不執(zhí)著",但這并不能否定這理論的價值。郭象等人能夠從理論上解決出世與入世的矛盾,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。這一理論對于人們的道德修養(yǎng),應(yīng)該說是具有巨大的啟發(fā)意義。我們作為一個人,必須生活在社會之中,為了謀生,我們必須從事各種各樣的事務(wù),這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的事實。在從事這些具體的事務(wù)時,如果我們能夠多一份超脫精神的話,我們就會少一份煩惱。絕對的"內(nèi)圣外王"和"不執(zhí)著"是沒有的,但相對地去做到這一點,還是完全可能的。
|
|
|



